雷子軒,14歲,先天性眼底黃斑病變患者,現(xiàn)就讀于惠州市特殊學校。她以超凡的音樂天賦和堅韌的毅力,在鋼琴演奏、聲樂、朗誦等領域屢獲殊榮,包括國際聲樂公開賽二等獎、德潤英才展演冠軍,并登上北京衛(wèi)視《天籟新聲》舞臺,被譽為“用耳朵看見世界的音樂天使”。

“我試一試”:一場師生間的雙向奔赴
鋼琴老師謝維克至今記得初見雷子軒的場景——瘦小的女孩坐在琴凳上,手指摸索著琴鍵彈奏自學的曲子,笑容像“穿透烏云的陽光”。面對這位特殊學生,這位廣東省十佳流行鋼琴演奏家坦言:“我沒有教盲童的經(jīng)驗,但她的熱愛讓我決定‘試一試’。”
這一試,揭開了奇跡的序幕。由于無法視譜,謝維克將每首曲目拆解成“聲音密碼”:先朗讀樂譜,再分小節(jié)示范,子軒則全程錄音,回家后反復聆聽、觸摸琴鍵重現(xiàn)旋律。為激發(fā)她的興趣,謝維克還創(chuàng)新教學,將枯燥的鋼琴基礎與即興伴奏結合。“她的耳朵像精密儀器,觸覺記憶更是驚人。”謝維克感嘆。
2025年的一場展演中,子軒自彈自唱《世界贈予我的》,清澈的嗓音與流暢的琴聲讓全場動容。謝維克在臺下濕了眼眶:“那一刻我明白,不是我在教她,而是她在教我何為生命的韌性。”
“草芽頂破黑暗”:從川中丘陵到嶺南舞臺
子軒的音樂之路,始于一場與命運的博弈。先天失明的她曾因視力問題被普通學校勸退,孤獨如影隨形。2020年,她毅然南下惠州尋找母親,進入特殊學校學習盲文。“盲文課本落在掌心時,我好像抓住了光。”她說。
聲樂老師杜娟回憶,子軒對音樂有種“饑餓感”——每周母女倆驅車三小時往返上課,她在車上也不忘練習;為掌握舞臺動作,她需通過語言描述想象姿態(tài),再反復調整到分毫不差。“常人練十遍,她練百遍。”杜娟說。
這份執(zhí)著終獲回響:學琴僅五個月,她登上北京衛(wèi)視;朗誦《春大》時,一句“草芽在頂破黑暗”讓觀眾淚目;在國際賽事中,她以原創(chuàng)歌曲《給我星辰的人》征服評委,成為惠州市特殊藝術教育的標桿。
照亮自己的太陽,也能溫暖他人。在同學眼中,子軒是“會發(fā)光的女孩”。藝術中心的老師告訴記者,她總主動幫助其他視障孩子,用玩笑化解他們的沮喪。“音樂是我的眼睛,我想帶更多人‘看見’美好。”子軒說。
她的母親始終是幕后英雄。從重慶到惠州,從求醫(yī)無果到陪女兒征戰(zhàn)舞臺,這位母親用車輪丈量出愛的里程。“每次表演,獎杯的光都先照到媽媽的眼睛里。”子軒在自述中寫道。
“點位如豆,連綴成川”:盲文鋪就的追夢之路
子軒的書桌上,一本盲文版《假如給我三天光明》被翻得起了毛邊。“海倫·凱勒說‘若注定看不見光,我便成為自己的太陽’——這就是我的座右銘。”她指尖輕撫著凸起的文字,仿佛在觸摸思想的脈絡。從四川方言到字正腔圓的普通話,從盲文零基礎到深夜蜷在被窩摸讀,這個女孩用指腹"閱讀"的速度,如今已讓老師驚嘆。
語文課堂是她最珍視的殿堂。當老師帶著同學們《蒹葭》《桃夭》時,子軒總挺直脊背,讓聲音在胸腔共鳴。“宮商角徵羽是中國人的音階,我的世界沒有色彩,但聲音里有永不褪色的畫筆。”她的吟誦視頻《蘆花》在網(wǎng)絡走紅,那句“西風吹來,花飛如雪”被網(wǎng)友贊為“比月光更皎潔的聲音”。
“琴鍵上的山河”:備戰(zhàn)“星海灣樂杯”的日與夜
此刻,子軒正為“星海灣樂杯”粵港澳青少年音樂展演全力準備。鋼琴前,她纖細的手指在《天堂》的旋律中起伏,如同白鷺掠過故鄉(xiāng)嘉陵江面。“六級證書只是起點。”謝維克老師透露,這次展演她將挑戰(zhàn)更高難度的原創(chuàng)曲目,把巴蜀童謠與嶺南民樂相融合。
備賽過程充滿艱辛。一段復雜的左手伴奏,她需要將老師的手勢轉化為觸覺記憶,再拆解成數(shù)百次重復練習。“錯音時她會咬嘴唇,但從不哭。”母親心疼地說。深夜的琴房常亮著燈,保安都知道:“那個盲姑娘又在加練了。”
問及對“星海灣樂杯”的期待,子軒彈起《我和我的祖國》,琴聲清越如泉:“參賽不是為獎項,是想告訴所有人——”她突然提高聲調,“黑暗里也能有星辰大海!”
采訪結束前,子軒忽然問道:“您知道為什么盲文叫‘點字’嗎?”不等回答,她自問自答:“因為再微弱的光點,連起來就是銀河。”正如她即將踏上的“星海”大舞臺,那里會有千萬束光,為這個以音符作畫的女孩照亮前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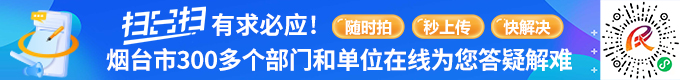


 2020年全國“放魚日”同步增殖放流活動在煙
2020年全國“放魚日”同步增殖放流活動在煙 山東滑雪高手匯聚“雪窩”煙臺 賽場飛馳比
山東滑雪高手匯聚“雪窩”煙臺 賽場飛馳比 2000余名民間藝人齊聚
2000余名民間藝人齊聚 以新姿態(tài)奔赴新征程
以新姿態(tài)奔赴新征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