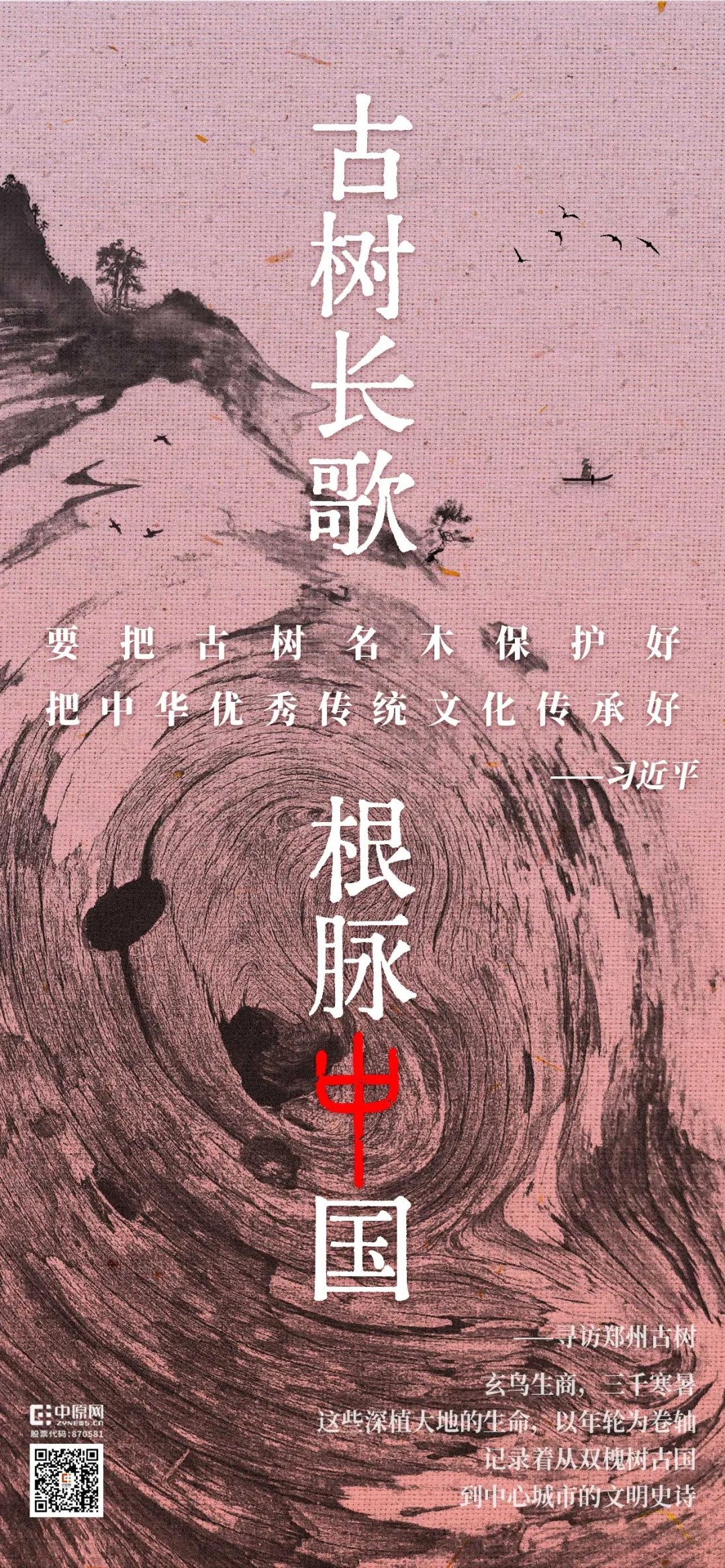
它被喚作“歪脖子”,在代書胡同已經(jīng)生長了200年。
這棵老槐斜插在兩棟居民樓之間,好似被時(shí)光抽走了脊梁。樹干早已變空,樹皮斑駁。
可每年六月,嫩芽總倔強(qiáng)地從枯枝里鉆出來,硬生生在鋼筋水泥的夾縫中撐起一把綠傘。

“我打小就見它歪著,那會(huì)兒胡同里還是泥路,一下雨就得趟著水走。誰能想到,這空心的樹疙瘩,竟成了咱們的‘樹堅(jiān)強(qiáng)’ 。”
聊起這棵“歪脖子”,77歲的白月桂說,“你們瞅瞅,它那樹身緊貼著樓房,離得近的地兒,不足半米。樹干彎彎繞繞到了二樓拐了個(gè)大急彎,就像跟人側(cè)著身子給空調(diào)外機(jī)讓道似的,就這樣還可勁兒往上躥呢。”
從黃殿坑到代書胡同
這條隱于鬧市的胡同,形成于明清時(shí)期,原稱“黃殿坑?xùn)|沿”,如果要提代書胡同的歷史就不得不提黃殿坑。
據(jù)老人們回憶,早在明清時(shí)期,黃殿坑就是鄭州城西南的一個(gè)重要地標(biāo)。那時(shí)的黃殿坑,地勢(shì)低洼,積水成潭,周圍居民常來此洗衣、洗菜,甚至游泳抓魚。隨著時(shí)代的變遷,黃殿坑經(jīng)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新中國成立前,黃殿坑有60多畝,水多坑深,隨著城市建設(shè)的推進(jìn),黃殿坑逐漸被填平改造,但地名與文化記憶卻沉淀下來。

● 王秀清 攝
黃殿坑所在的區(qū)域如今已煥發(fā)出新的生機(jī)。以代書胡同為例,它是一條曾經(jīng)因文人聚居、代人書寫呈文狀子而聞名的老胡同。代書胡同整體呈Y字形,東起管城街,西至營門街,南連西大街。
在明朝洪武元年(1368年),當(dāng)時(shí)鄭州在州治西南創(chuàng)建了管城驛。驛站的北邊,就是現(xiàn)在的代書胡同,再向東北不遠(yuǎn),就是州府衙門。代書胡同正是得此地利之便,成為一些訟師、及代人書寫呈文、狀子的文人們聚居的地方。

● 鄭州文物局 王羿 攝
那些識(shí)字不多的百姓,便向聚居于此的文人秀才求助,代筆書寫家書、狀子、呈文,久而久之,“代書”成了這片土地的文化標(biāo)簽。至近代黃殿坑填埋后,“代書胡同”的名字卻沿用下來,成為老城記憶。
而這棵被居民嫌棄過的歪脖子樹,也在看著代書胡同的人來人往,歲月變遷。
兩棟樓夾縫中的第三條生命

在北下街代書胡同社區(qū)書記龔猛的記憶中,這棵古樹曾是“麻煩制造者”。
它斜插在不足三米寬的樓間通道,樹冠遮蔽了半邊道路,槐樹的身子,歪斜得厲害,被好幾根鐵支架牢牢地支著。“早年地面全硬化了,樹根被‘捂’得喘不過氣。更糟的是,樹干內(nèi)被白蟻掏空,眼看就要不行了。”龔猛說,這棵古樹已被園林局列為瀕危古樹。

● 資料圖
登封市文物局遺產(chǎn)科專家靳紅軍的診斷揭示了其“三大致命傷”:根系窒息(硬化地面封死呼吸通道)、空間擠壓(兩側(cè)建筑嚴(yán)重侵占其生長空間)、樹洞處理不當(dāng)(發(fā)泡膠封堵導(dǎo)致內(nèi)部腐爛加劇)。“這情形,堪比人的窒息、骨折加感染。”
然而,生命的韌性超乎想象。即便木質(zhì)部朽壞中空,樹皮下的分生組織仍在不知疲倦地工作,每年春天都會(huì)頂出嫩芽。
白月桂老人清晰記得,1998年第一次小區(qū)改造時(shí),不少居民對(duì)這棵“礙事兒”的老樹有意見。可她卻不這樣想,“它比人活得久!黃殿坑填了,路好走了,可樹還在。它看過的世面,比咱們多。”
代書胡同上演“生命讓行記”
2020年,代書胡同迎來歷史性蛻變。在老舊小區(qū)改造工程中,“一切為古樹讓行”成為共識(shí)。
“修地鐵都懂得為古槐繞個(gè)彎兒,咱改造自己的家園,還能容不下一位‘歪脖子’的老街坊?”龔猛說,這不僅僅是一次改造,更是一場(chǎng)精心呵護(hù)的生命保衛(wèi)戰(zhàn)。

● 資料圖|為古樹加固
在鋪熱力管道時(shí),為了避免樹根受傷,熱力管道整體架空,為盤根錯(cuò)節(jié)的樹根騰出舒展空間,讓古樹的根系得以重獲自由呼吸的機(jī)會(huì)。

● 圖|為古樹讓行,架空熱力管道

● 資料圖|開辟新路,分流居民
道路規(guī)劃也做出重大調(diào)整,進(jìn)行人員分流,開辟另外的活動(dòng)區(qū)域,減少居民在樓宇間隙的流動(dòng),為古樹生長開辟出專屬通道。

● 圖|安裝監(jiān)控
另外,古樹的對(duì)面還安裝了監(jiān)控探頭,24小時(shí)守護(hù)著它。定期輸注的營養(yǎng)液順著導(dǎo)管緩緩滲入根系,恰似為年邁的長者輸送生命的活力。
為了讓古樹更強(qiáng)健,一項(xiàng)名為“復(fù)壯”的工程悄然進(jìn)行。
據(jù)管城回族區(qū)市政綠化服務(wù)中心的老師介紹,在樹冠遮蔽下的硬化地面,精準(zhǔn)鉆出12個(gè)碗口粗(直徑110mm)、深80厘米的探孔。孔內(nèi)埋設(shè)帶孔PVC“呼吸導(dǎo)管”(上覆地漏),填充特制營養(yǎng)基質(zhì)和促根殺菌藥液。這些間隔1.5-2米的“生命通道”,顯著改善了透水透氣性,疏松板結(jié)土壤,如同為古樹進(jìn)行深度“強(qiáng)身健體”。

● 圖|“古樹醫(yī)生”正在“藥浴”消毒
工人師傅化身“古樹醫(yī)生”,仔細(xì)清除樹洞內(nèi)有害填充物及腐爛組織,保持“傷口”開放通風(fēng)。接著,采用稀釋的環(huán)保殺蟲殺菌劑(噻蟲嗪、農(nóng)用硫酸鏈霉素、已唑醇)進(jìn)行高壓“藥浴”消殺。待“傷口”干燥,涂抹防腐藥劑混合固化劑深層保護(hù)。最后,巧匠用陽離子丁膠乳材料,在外部精心勾勒仿木質(zhì)紋理。為修復(fù)高處3平方米的創(chuàng)面,甚至專門搭起鋼管架。
“每一道工序,都傾注著對(duì)這位老友的深深敬意。”龔猛望著古樹又一茬的新芽說,“我們聽相關(guān)專家說,對(duì)于瀕危古樹,只要有生命跡象施救措施得當(dāng)就有可能救活,過了危險(xiǎn)期生命體征恢復(fù)以后,一般情況下三到五年以后就會(huì)枝繁葉茂。”
活著的鄉(xiāng)愁 老樹又發(fā)芽
白月桂拍著樹干:“俺們家三代人都在這個(gè)院兒扎著根,老輩人常說啊,這棵樹,就是俺們胡同的‘主心骨兒’。”她頓了頓,目光望向枝干,“那些擺攤兒寫信的老先生們,早都不在人世了,可‘代書’這名兒啊,這棵老槐樹還替他們記著。”
我們走訪街坊四鄰時(shí),聽院子里的老人說起它,話頭里雖也摻著些埋怨,但多數(shù)是打心眼里地欽佩:”別看它彎了腰桿兒啊,可那架子骨,硬是沒塌過。”
這勁頭,就跟胡同的老百姓一個(gè)樣。以前的日子再作難,大家也可勁兒往前拱,日子也越過越有盼頭。

代書胡同的改造,折射出老城更新的溫度與智慧。
當(dāng)鋼筋水泥的叢林不斷擴(kuò)張,這棵空心的古槐樹,宛如城市快節(jié)奏發(fā)展中的一個(gè)“逗號(hào)”,它讓改造的步履為生命而慢下來,也讓人們看見了城市更新中傳承與發(fā)展和諧共生的可能。
“拆舊建新容易,難的是把這份煙火氣里的念想留住、捂熱。”龔猛的感慨發(fā)自肺腑,“它就那么站著,看著街名沒變、老鄰居還在、新樓房蓋起、車來人往不停。它不是絆腳石,是連著過去和今天的一根‘老藤’,讓我們這輩人、下輩人,都能順著它摸到這條胡同的‘根’。”

古槐空膛為何不死?
靳紅軍給出了形象的解釋:“樹活一口氣,這‘氣’在皮,不在心。”他指著枝頭鮮嫩的芽苞,“樹皮下的韌皮部,是把葉子里造的‘甜水’(養(yǎng)分)往根上送的‘糧道’;里面的木質(zhì)部,是把根吸的‘清水’(水分養(yǎng)分)往枝葉運(yùn)的‘水路’。只要這兩條命脈沒斷透,哪怕心空了,它也能在傷疤上,憋出一股子新勁兒,再活他個(gè)百年!”
這棵空膛的古槐,用它沉默的堅(jiān)守和年年新發(fā)的綠意,穩(wěn)穩(wěn)地托起了這條老胡同煙火深處,那份沉甸甸、暖融融的,名叫“鄉(xiāng)愁”的重量。
「 編者按 」
“要把古樹名木保護(hù)好,把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傳承好。”習(xí)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,為守護(hù)自然與文明的珍貴遺產(chǎn)指明方向。
2025年3月15日,《古樹名木保護(hù)條例》正式施行,這部我國首部針對(duì)古樹名木保護(hù)管理的行政法規(guī),以法律的堅(jiān)實(shí)臂膀,為“綠色國寶”筑起全方位守護(hù)屏障。每一棵古樹都是活著的歷史典籍,守護(hù)它們,就是守護(hù)文化根脈,延續(xù)文明薪火。
“前人栽樹,后人乘涼”的古訓(xùn),在鄭州這片熱土上化作跨越時(shí)空的生命交響。從阡陌交錯(cuò)的農(nóng)耕時(shí)代到鋼筋森林的現(xiàn)代都市,鄭州的古樹守護(hù)著一代又一代人,忠實(shí)地記錄著城市版圖的滄桑巨變。
中原網(wǎng)推出“古樹長歌·根脈中國——尋訪鄭州古樹”大型系列策劃報(bào)道。讓我們一起,去看看鄭州的古樹,就像去見一個(gè)久未謀面的老朋友,探尋它們所蘊(yùn)含的歲月故事。
全城尋樹
您家巷口可有會(huì)講故事的百歲樹翁?
一棵古樹,一段往事,一腔鄉(xiāng)愁
如您有古樹線索可與我們聯(lián)系
我們一起守護(hù)城市年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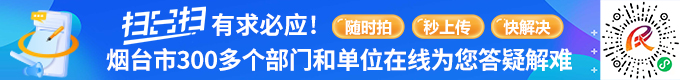


 2020年全國“放魚日”同步增殖放流活動(dòng)在煙
2020年全國“放魚日”同步增殖放流活動(dòng)在煙 山東滑雪高手匯聚“雪窩”煙臺(tái) 賽場(chǎng)飛馳比
山東滑雪高手匯聚“雪窩”煙臺(tái) 賽場(chǎng)飛馳比 2000余名民間藝人齊聚
2000余名民間藝人齊聚 以新姿態(tài)奔赴新征程
以新姿態(tài)奔赴新征程
